那天,我推開禮堂的門,一邊輕手輕腳進入現場,一邊豎起耳朵聆聽台上那把慈祥的聲音在說什麼——“好吧!我來回答這個問題。所謂‘彼此的能量’,是在人與人之間發生的事。它不是單向的交流,也不是純粹從智性層面發生的互動。雖然我還在學習中,對資訊科技不是很熟,對人工智能也不太瞭解,但我認為與人工智能交流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,因為那樣的溝通是屬於理性與邏輯層面的。而人與人之間的溝通,像是你我現在的對話,所涉及的不只是語言本身,還包括了‘關係’的存在。所以,這裡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,我們能與人工智慧建立一段關係嗎?如果可以,那會是什麼樣的關係?這個問題,我無法回答。”我想,我錯過了一場精彩的分享。

那把聲音的主人——Liese Groot-Alberts是今屆亞太安寧療護網絡大會Cynthia_Goh獎的得主,她投入安寧療護已有半個世紀,見證了這個領域的成長與發展,稱她為這個領域的老前輩一點也不過。在經歷了疫情的風雨後,正當安寧療護在本地積極發展的這個時候,麗絲的心得分享著實給大家增加了勇氣與動力。從她口中說出的,並不是什麼遠大的目標,也不是先進醫療系統,她拋開僵化的模型,帶我們回到人與人之間的當下。告訴我們,安寧療護始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。

●真實關係,來自聽見
麗絲認為,團隊或人員在陪伴病人,為病人進行一切安寧照護行為之前,最重要的是先與對方建立關係, 因為關係與慈悲是不可分割的, 慈悲是一種能量, 它只能發生在平等的關係中。“ 當我們自認為自己‘ 比較懂’ 、‘ 比較知道對方需要什麼’ , 就會不自覺地進入一種我稱之為‘ 專家病(expertosis)’的狀態,當專家病出現,彼此之間就產生了距離,照顧與慈悲的能量也在那一刻被切斷。”
聆聽(listening) 與聽見(hearing) 是建立關係的工具, 是以時間來建立一份連結(connection)。聆聽是聽對方說出口的話,而聽見是聽那些對方沒有說出口的話。當我們投入整個人,以身、心、靈及思想去接收與感應對方時,連結才能產生。連結不是牽手或安慰,而是一種無條件的尊重與接納。
若我們不是抱著“理解彼此”、“明白對方”的本意去聆聽,那我們就聽不見對方。在對方說話的當兒,我們腦子裡開始建構我們的回應方程式,在那個時候我們是在截斷與對方的連結,在脫離對方,我們就聽不見對方,就沒有與對方同在,而是與自己同在。聽見是需要練習的,學會傾聽和等待,聽完全部後往內在尋找回應,再將它往外傳達。當我們這麼做時,我們是活在當下的。“當我們陪伴那些正與死亡共舞,或與死亡掙扎的人時,最重要的是活在當下,唯有真正的全神貫注於當下,我們才能與對方建立真實的關係與連結。”

●卸下預設,走進當下
當我們踏入和某個我們所關心的人的關係時,我們進入的是對方的能量、對方的存在,這片領域是神聖的。依照古老儀式,在踏入聖地時,我們需要脫鞋。同樣地,在第一次與對方建立連結時,我們也得在心中象徵性地“脫鞋”,就像我們回家時那樣,我們不會把外面的髒污帶進家中,外在與內在是分開的。
當我們還沒有真正進入關係時,我們是穿著鞋子處於“共同地帶”上,這時我們先停下來聽聽自己的內在聲音。問問自己:我現在內心發生了什麼事?我準備好了嗎?是不是正帶著某個理論、方法或預設進來?若有就先把它擱在一邊,提醒自己,現在的重點是“此時此刻的人”。這樣的“脫鞋”,讓她學會要同時尊重內在的聲音與外在的聲音。真正的同理與連結,不只是技巧,更是一種內在的覺察與誠實。
麗絲的這番話讓我聽見她對關係的用心、認真與重視,她尊重對方,也尊重自己。

●看見自己,也看見他
麗絲認為安寧療護人員真正的挑戰來自於本身的內在世界。“如果想要陪伴垂死的人,最好先處理好自己的爛事(Clean your shit)。”生死學大師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羅斯曾如此忠告麗絲,一開始她覺得這話有點粗俗,但後來她聽懂了良師的話——在照顧別人之前,先處理自己的創傷。“我們都是‘帶著傷的療癒者’,我們可以把自己的創傷變成我們共同成長的肥料,轉化為滋養的力量,因為我們不只是帶著破碎來到這裡,也帶著力量與成長的渴望來到這裡。”
“如果我們沒有處理自己的傷口、沒有自我療癒,就會開始與自己的感受切割。當我們切割自己,我們也就無法與別人連結,那關係就不存在,連結也斷了。那樣的話,我們變得容易只站在病床尾端,與病人保持距離,因為這樣比較‘安全’,而不是走到床邊、陪在對方身旁。”
她說痛苦和不舒服感常常伴隨同理心而來,所以當情況艱難時,我們很容易選擇退縮,如果不能面對這份內在的脆弱,築起一道牆,把自己封閉起來,那麼同理心就無法流動。因此,麗絲深深希望自己和所有安寧療護人員都能夠持續地學習“自我慈悲(self-compassion)”,能夠溫柔待己,就比較不會在人際關係中消失、退縮、不見,不讓自己在他人面前變得隱形,也不讓自己在自己面前隱形。看到與看見我們關心的人、他們的家人親友社區,同時也看到和看見我們自己。

●深度時刻,魔法發生
我十分喜歡麗絲對於時間的描述,她說時間本身是一個神話,同時也是一種障礙。時間以兩種方式存在,一種是長度,另一種是深度。時間的長度指的是“線性的時間”,也就是我們常說的“五分鐘、一小時”這種時間段,這種存在是很淺薄的,因為在這樣的時間裡,我們的腦袋已經在安排接下來要做的每一件事,一件接著一件、線性地往前走。而時間的深度是“當下的全然在場”,在這種時間裡,我們完全地投入於當下的關係、當下的連結,有深度的時間是豐厚、飽滿的,在這種時間中,時間彷彿不存在。
她說“聽見”是以時間來建立一份連結,但往往當別人對我們吐露他們的心情或內在感受時,我們就算沒有說出口,心裡也會這麼想:“我忙到昏天暗地,根本沒有時間理那些雞毛蒜皮、虛無縹緲的東西”。麗絲指出,“聽見”跟花多少時間沒有關係。“聽見”所需要的,不是時間的長度,而是時間的深度。
她舉例,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,一群人坐在一起花了一兩個小時討論事情,卻什麼也沒討論出來,這樣的時間是空泛、淺薄的,然而如果我們是和對方同在一個當下,一個瞬間裡,彼此深入其中,只消片刻就能做到很多事情,做出許多改變。
“你可能只跟某人相處短短五分鐘,甚至兩分鐘。但因為你全心投入、真正在場,你們彼此就真的‘在一起’了。這時,魔法就會發生,關係可能就在這樣的瞬間裡誕生與成長。”現場在座的每一個人,無不被她對於時間的詮釋拍案叫絕。
回到現實中的時間限制與界線,她表示,也許我們真的只有五分鐘能陪對方,那也沒關係,只要清楚地表達出來,比如告訴對方:“我現在就在這裡,這五分鐘是完全為你而存在的。接下來我會離開一下,之後會再回來”。這樣的話語能讓對方感受到被重視、被陪伴,哪怕時間很短,那已是有品質的陪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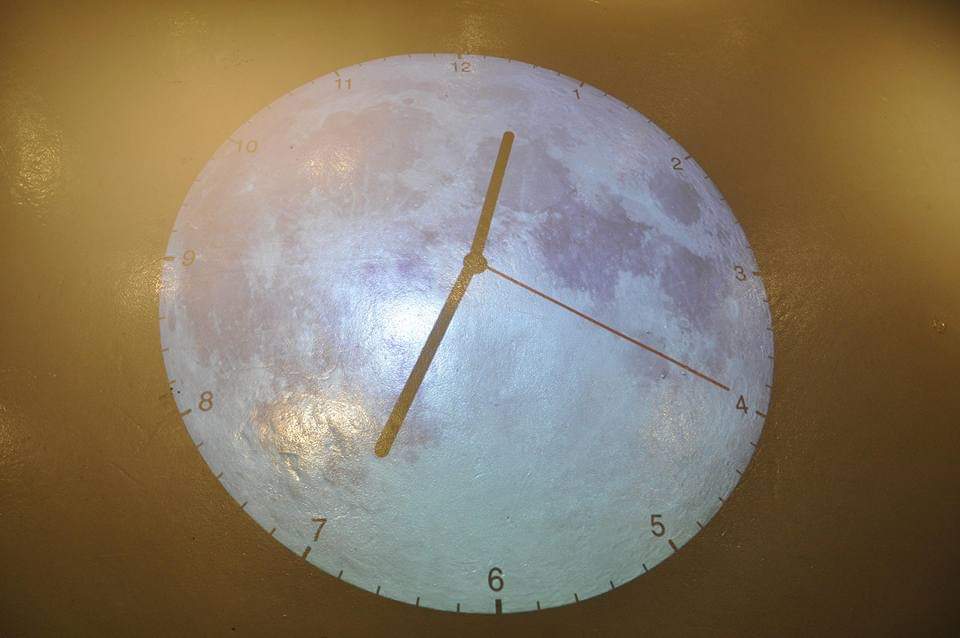
了。”——Liese Groot-Alberts。

報道:戴舒婷
 砂麼東東
砂麼東東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