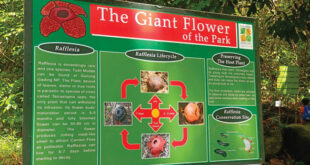库克船长这么说过:“ 我不止要比前人走得更远,而是要尽人所能走到最远”,而泰戈尔说:“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越远。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泊,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”,那么,我们四处旅游到底是要逐远还是求近?这点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。那旅人翻看硬盘里保存的照片,一条又一条的路重现眼前,这才发现这几年旅人选择的不是地方,而是路,可以走得舒畅的路。
●大洋路 梦开始的地方
来到大洋路,我开始有了徒步旅行的想法。大洋路(The Great Ocean Road)是澳洲东海岸维多利亚省的一条行车公路,全长约243公里,沿着巴斯海岸建于悬崖峭壁中间,参与建设的三千余人中,有不少是参战老兵,他们用了14年时间,为这段纪念一战牺牲者的公路,付出艰辛的汗水,就像他们上战场时所抱着的理想一样,希望为家为国开出一条康庄大道。

从墨尔本市乘小旅巴出发,靠左侧坐的我,透过宽大车镜看见巴斯海峡,延绵无尽的海岸线,没有尽头的蓝色水布,让我感受到海广大的胸襟,接纳了我带来的一身污浊。心里不由地觉得,这样的地方只是经过和短暂逗留太可惜了,但我不会骑单车,也不想在国外开车,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细细品味大洋路呢?有了,人类最原始的移动方式——徒步。

于是我开始计划与想象,下一次去大洋路,要在沿途乡间小镇停歇——托儿坎、安吉西、洛恩、阿波罗湾、坎贝尔港,还要再看看十二使徒岩、洛克阿德大峡谷、奥特威角灯塔,不是到此一游,而是用脚去认识它的每一寸。尽管时间过去了许多年,这个计划尚未实现,但是每一次从荧幕看见大洋路的照片,想起那一年的海风,心里都很确定,有一天我会回到那里。

●台11线 收集勇气的地方
台11线花东海岸公路也称海线,是台湾一条联接花莲县与台东县沿海城镇的省道,全长177公里。徒步花东海岸公路,可以说是我为了徒步大洋路做的第二阶段预习。从花莲市乘公车离开市区后,我随机按铃下车,从一个叫水琏的地方开始没有目的地,没有设时地步行,那时候背包里带着的是一张地图,还有吴明益的《家,离水边那么近》。那本书写着他骑行和徒步花东,去听海听河听溪,去学习当地的人文与自然的路程,我透过它(他)初闻花莲,于是带着预习与实践的心出发,开始了用脚旅行的章页。

我还记得11月的秋天,太平洋蓝得多炫耀,太阳毒辣得多不像话,一个吸引我,一个赶我走。我左手是太平洋,右手是中央山脉,这两个名字叫我感觉自己被世上了不起的部分给包围与陪伴,何其幸福。炎日下,支持我一直走下去的,是一路上不断对我高喊的路人,一声又一声的“加油”,毫不吝啬的打气,还有他们好意施舍给我的冰水,都让心里那股倔强不退缩。旅途中有一幕,我专心于双脚的动作,突然抬头看见的是正前方的长路,长路尽头是海洋。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,老天在告诉我,我要走的路很长很长,但是后面一定有礼物。

这一路,我走到花莲与台东的交界处,然后乘公车回花莲市。回程的路上,我从车上用眼睛回顾我走过的一路,太平洋还是蓝的,太阳还是毒辣的,我开始想哭。回国后,因为硬盘故障,那一路的照片都没有了,但是,那一路上我见过的人、那天的日温、蛤蜊汤的味道,还有小腿上的痛,没有和硬盘一起消失。

●没有名字的路 顶级星光大道
老谢车马店没有地址,我将写着“香格里拉县城6公里的草原上”的笔记交给司机,结果还真的能找到,在那里呆了几天后我发现,那里的路都没有名字,民宿负责人给我的卡片上,地图是以景点、加油站和机场为标记,唯一有名字的路就是滇藏公路,而这条公路相当与泛婆大道的等级,每次打车回民宿,我只能告诉司机“石卡”,仿佛那雪山就是我家。

我去过香格里拉县两次,两次我都住在离市区有点距离的老谢车马店,司机总是问,为什么住在交通这么不便的地方,找吃很难。确实很难,我得走很远的路去求藏民或是名宿员工帮忙想办法才能吃到便饭。然而,如果你见过那段路,你就会知道走再远的路去找吃都是幸福的。

那条无名路在石卡雪山下,道路左右两旁是一望无际的草原,草原间有土石路通往石灰盖的民宅,无名路北面是石卡雪山,南面是连绵山峦,我每天都在牛羊、蒲公英、铜铃声和冷风的陪伴下,在这条路上散步一两小时,我和世界一起从白天进入黑夜,所看到是大草原、大山、辽阔蓝天,入夜后景色换成满天星斗,这里没有路灯,晚上走在这路上,就是名符其实的星光大道,这比山珍海味还值得,不是吗?第一次入住老谢之前我并不知道它有这样的环境,住了之后,第二次我就为了这条路而去。同样的,我告诉司机去石卡。

●山体上的细线 路的深层意思
脚程开始前,接驳车从飞来寺载我到西当村路口,滇藏公路经过山谷和澜沧江,公路由石头铺成,路途非常颠簸,于是我将注意力放在窗外风景上,不然很容易晕车,途中我看见对面山体腰间有一条细长的线,起初不知道那是什么,后来距离拉近了才看得出那是山路,我立刻心想,夭寿咯,谁会走那样的路,难道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吗?


四天后,当我走下山,转身回头给山鞠躬时才知道,原来我所走的就是那条山腰的细线,原来真的没有第二条更好、更安全的路可以走,雨崩村和其他村的村民拒绝让政府把路开到村里,因为梅里雪山是座不可侵犯的圣山。因此,村民若有事要到城里,或是要运送物资,都得走这条山路。依着山腰开辟的这条路,是藏民一手一脚自己凿出来的,我在徒步的路上遇见许多修路的藏民,有些年纪挺大的。每次与他们擦身而过时,我都合掌对他们说“扎西德勒”。想到自己脚下的路虽不好走,却是他们一寸一寸凿的,就觉得自己抬不起头。

下山后,我再一次在接驳车上看这道山腰小路,刚好车上的收音机播放着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,歌词唱着“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,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”,我举起单眼遮住脸孔,眼泪就在相机后面流下来。
●自然步道~ 回到当下的路
没有人工添加物的路,这是我在我城追逐的路。2020年,疫情一度好转,我城的行动管制令改为复苏行动管制令,我立刻往山里去。奈何人人都和我一样,国家公园一大早就人满,我进不去,正想着要打道回府之际,高敏感的我被脚底下的触感给打住,脚似乎有它自己的记忆,隔着鞋底碰触到这些天然物质时,脚醒了过来。那一刻我才发现,原来除了芬多精,除了森林的清新气息,除了虫鸣鸟叫之外,森林步道还以另一种方式俘虏我。

被唤醒的脚变得不安分起来,我知道若我没满足它,接下来那几天心一定会牵挂,于是我往另一边的森林去,打定主意起码要走个一小时才甘愿回家。果然,当双足真正地踩在石头、土壤与树根上了,它雀跃得停不下来,仿佛只有走在这样的路上它才活着。这些有机物形成的路,给了我一种与环境连接的感觉,唯有碰触到它,才觉得自己是在世界里。

人造的路平坦好走,走起来也轻松,即使不看着走,也能走到想去的地方,所以我们能一边看手机一边走动,而像森林步道这样一上一下一高一低,凹凸不平的路,我必须一直看着,配合路况协调手脚动作才能走好,走在这样的路上,我身在心在。我想这是为什么脚能记住那触感的原因——因为我好好地,用心地走每一步,我用脚和地方沟通。
《我是背包客》
文、图:戴舒婷
 砂麼東東
砂麼東東